莫言终于出新作了——一下子在第9期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了剧本《锦衣》,加七首诗。这至少让读者的好奇心和期待感在数年之后,稍稍满足了一下,让那个“诺奖魔咒”的魅影暂时退到了远处。

莫言
还是那个莫言,那个一向奇幻而诙谐、接通着乡土民间的莫言,那个满带着烟火气息、牵连着高密东北乡根根须须枝枝蔓蔓的莫言,那个来自地方性的原汁原味与五花八门的、一向有着蓬勃感性和丰沛戏剧感的莫言。从小处说,他以此再次印证和强调了他自己的写作风格,证明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戏剧能力,强调了他鲜明强烈的戏剧性追求与诙谐感的诗意;从大处说,他是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,不经意而又实实在在地延续了纯文学意义上的当代戏剧——这种古老艺术的气脉。从他的《霸王别姬》《我们的荆轲》《蛙》,到这部《锦衣》,他的戏剧创作颇有可观之处,更兼他几乎用了“戏剧体”写成的《檀香刑》,还有更多具有浓烈戏剧性的长篇,莫言构成了在文体与形式、语言和美学上的另一个现象。他再次用不凡的创造力证明,纯文学意义上的戏剧乃至戏曲并没有远逝,关汉卿、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气脉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代。 莫言应邀题写的篇名
莫言应邀题写的篇名
似乎话说得有点大了。我的意思是,依然可以靠着杰出作家的创造力,来延续文学的核心要义,包括戏剧与戏曲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,包括小说本身的戏剧禀赋,叙事的戏剧性与诗意等等。这些问题事关传统、艺术的复杂的本体论问题,需要择机细加讨论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莫言在当代作家中,在文体方面是最“无边界”的一位,他对艺术形式的混合杂糅与创生再造的能力,实在是令人瞠目。
《锦衣》叙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:清末之际,正值民不聊生,百业凋敝,污吏横行,妖孽四起,留日的爱国青年秦兴邦和季星官乔装夫妻潜回乡里,图谋举事。路见大烟鬼宋老三沿街卖女宋春莲,季星官一则感慨不平,二则一见钟情。但很快,二人被捕快爪牙识破,秦兴邦逃走,季星官诈死潜藏。中间穿插了顺发盐铺掌柜,季星官的寡母,媒婆王氏及其官府鹰犬的侄子王豹,还有卖官鬻爵、鱼肉乡里的高密县令庄有理和庄雄才父子的重重纠葛。王婆、王豹因图谋盐铺钱财,设计让季母为远在东洋留学的儿子先行娶妻,致使季母让儿媳春莲与一只公鸡成亲。而王豹与庄雄才均垂涎春莲美色,数度前来纠缠,春莲誓死抗争,危急时刻季星官潜回家中为春莲疗伤,两情缱绻,终成夫妻。不料为偷听者王婆告发,庄氏父子带兵前来捉拿,正好被秦兴邦和季星官所发动的义军击败,王豹等爪牙则乘势投机反水,捉住庄氏父子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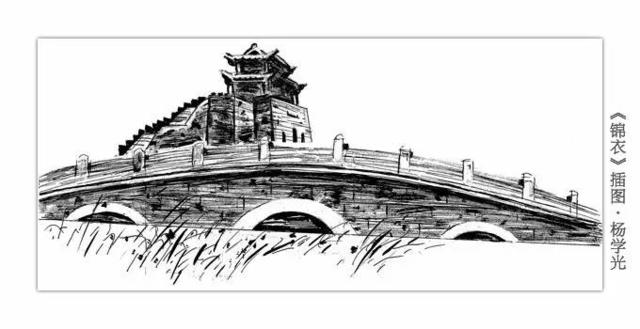 剧情的混合意味非常明显,也像是《阿Q正传》或者《茶馆》,甚至莫言自己的《檀香刑》中的某些场景:有革命和近代史,更有民间生活场景、传统戏曲原型等,互相杂糅,成为一个离奇曲折、跌宕起伏的故事。以作者自述的话说,“故事原型”为“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,成为亦真亦幻之警世文本”。这里有英雄救美,有移花接木,有善恶必报,也有偷梁换柱,种种旧戏中常见的结构与主题,在其中都有体现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,它再度深入探究和处理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社会问题,既生动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,披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,又从文化、制度、伦理甚至文明的层面,深入揭示了历史、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。可以说,莫言以他独有的戏剧性笔触,通过人物的对话,活脱脱将其彰显无遗。
剧情的混合意味非常明显,也像是《阿Q正传》或者《茶馆》,甚至莫言自己的《檀香刑》中的某些场景:有革命和近代史,更有民间生活场景、传统戏曲原型等,互相杂糅,成为一个离奇曲折、跌宕起伏的故事。以作者自述的话说,“故事原型”为“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,成为亦真亦幻之警世文本”。这里有英雄救美,有移花接木,有善恶必报,也有偷梁换柱,种种旧戏中常见的结构与主题,在其中都有体现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,它再度深入探究和处理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社会问题,既生动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,披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,又从文化、制度、伦理甚至文明的层面,深入揭示了历史、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。可以说,莫言以他独有的戏剧性笔触,通过人物的对话,活脱脱将其彰显无遗。 当然,民间生活场景依然是重要的。买卖婚姻与婆媳关系,说媒拉纤与混世青皮,近代中国的衰败与流氓文化的盛行,其相辅相成的关系,在这部剧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当然,民间生活场景依然是重要的。买卖婚姻与婆媳关系,说媒拉纤与混世青皮,近代中国的衰败与流氓文化的盛行,其相辅相成的关系,在这部剧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艺术的谱系上,《锦衣》的复杂性更是难于匆促说清。窃以为,其中有关汉卿和莎士比亚的影子,有《水浒传》的胚子,有鲁迅和老舍的骨架子,更有民间戏曲的各种元素与壳子。感觉它在奇迹般地复活地方性戏曲这样的质素与形式。若是吟咏起来,完全可以套上不同戏曲的唱念做打,再现一台精彩大戏。按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,现如今没有什么人会对这般艺术类型抱有信心,但莫言恰恰就以他点石成金的才能,彰显出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。 还有风格。在我看来,莫言一直在刻意地用“障眼法”或者喜剧性,来处理或者中和其作品的批判力与悲剧性。他成功了。无论是《酒国》《檀香刑》还是《四十一炮》《生死疲劳》等,都是如此。或许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欲扬先抑和“锦衣夜行”,当然也是更高意义上的“警世奇幻”,或者艺术的辩证法。
还有风格。在我看来,莫言一直在刻意地用“障眼法”或者喜剧性,来处理或者中和其作品的批判力与悲剧性。他成功了。无论是《酒国》《檀香刑》还是《四十一炮》《生死疲劳》等,都是如此。或许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欲扬先抑和“锦衣夜行”,当然也是更高意义上的“警世奇幻”,或者艺术的辩证法。
莫言有着令人惊讶的感性才华,在任何情况下,他的观念都不会压倒其艺术形象。他的传神之笔,寥寥几下就能够点活一个人物,激活一种性格,展开一种话语或腔调,使之在他的艺术王国中披挂上阵,肩负起讥讽世事、鞭挞人性的激越使命。《锦衣》中的人物,尤其如是。
(编辑:月儿)








 假洋膏药年销过亿元,平台监管不能失灵
假洋膏药年销过亿元,平台监管不能失灵 自动电饭锅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……17种网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公布
自动电饭锅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……17种网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公布 口腔诊所常见的“中华口腔医学会”,花钱就可成会员!乱象曝光
口腔诊所常见的“中华口腔医学会”,花钱就可成会员!乱象曝光 答非所问、鸡同鸭讲—— AI客服发展迅猛 “软”服务不能太“软”
答非所问、鸡同鸭讲—— AI客服发展迅猛 “软”服务不能太“软”